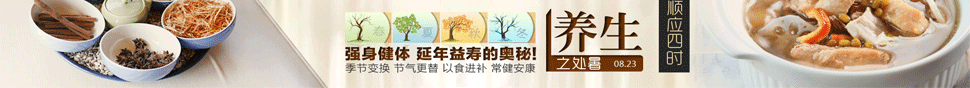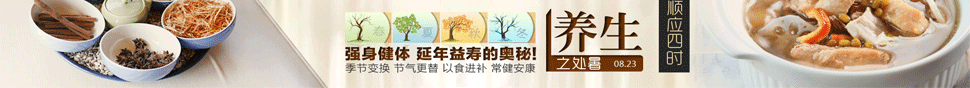#生态文明建设#3月17日下午一点,由中国绿发会政研室牵头举办的海南“买卖穿山甲环境侵权案”线上研讨会如期举行。来自环境法、诉讼法、生态保护、检察机关、等领域的相关专家及专业人士,将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充分的探讨和交流。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肖建华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发表了以下几点意见,现将王老师的发言整理、分享如下。前面几位发言人都讲的很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来看这个案例,对我也很有启发,现在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公益诉讼活动对于整个社会重视野生动物保护、重视穿山甲保护有着很大作用。现在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认识比原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个案例所体现出来的我们对穿山甲的保护力度还是与原期待的力度有很大的距离。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责任的承担主体。在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当被告作为共同侵权人,他们的内部责任就要有一个法院判定,判定的方式是这几个人要共同承担责任。那么,要用什么方式来表示责任的承担?判决书的做法一般有三种:一种是共同责任,共同责任在民法当中没有,共同责任比连带责任要更加的刚性,就是说每一位被告都应该无条件的偿还全部的责任;连带责任需要列出某位被告对前述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有某种次序的显示;按份责任是第三种,各位被告分别承担同样的义务责任,这样各位被告的处罚份额就都是确定的了。那么,本案当中这几位被告对于穿山甲的损害、对生态的损害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请求权基础的问题,根据有关的《民事诉讼法》条款,我们作为公益环保组织起诉的应该是环境污染、环境侵权诉讼、生态侵权诉讼等类的案例。此次案例就是司法解释扩大了生态侵权,我们应该以危害环境或危害生态作为基础,来请求有关的责任人承担责任。我们能最直接使用的法律是《环境保护法》,还有《野生动物保护法》,这两部法律的表述是保护生态文明,还考虑到了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等等,所以这两部法律共同体现了生态保护的功能。被告四食用穿山甲的行为,到底是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行为,还是对环境、对生态保护有危害的行为?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实际是构成了竞合。因为,无论经过多少次买卖,最后导致穿山甲死亡或者存活,买卖目的都是为了食用,只是存活的穿山甲在最终售卖时的价钱高于死亡的穿山甲。《野生动物保护法》关于生物制品和动物的尸体的保护是没有与运输、储藏之分的,穿山甲死亡的后果给生态造成的影响是损害了《环境保护法》所保护的生态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曹教授和高教授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分解开来,最后从这两部法律保护的法益与四位被告的作为结合来看,是可以把四位被告都做作为共同被告,让他们都当侵权人,对穿山甲死亡的后果、对于生态危害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尽管他们没有合意,未共同参与、直接故意杀害穿山甲,但是对于造成的后果都是存在责任的。法院判决对此也有分析,但没有对请求权基础的分析,在这点上做的不够细致。以上是我关于责任承担的划分的想法,这方面可能论述的更多一些。第二个问题,关于穿山甲的经济价值。刚才几个教授都谈到了,我认为判决书所判定的数额太低,甚至连穿山甲被买卖的价格都没有达到,先不说其他的价值有没有被考虑到,单就生态价值就根本没有被考虑到,这确确实实是环境保护法的一个退步。第三个问题则是关于怎样来让侵权人承担责任。各位专家都谈到了生态修复,其实中国法院对此已经做得很成熟了。就以环境受侵害来说,比方对于垦荒、破坏树林的,让侵权人去重新植多少棵树,已经形成很固定的做法了。但是,动物被杀害了,侵权人又不能复活动物,我认为可以让侵权人去森林里看护动物,判侵权人用一定的工期来看守动物,或者是让侵权人挖白蚁,让他知道在生态系统保护中自己能参与多少,就能知道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了。这是对侵权人的教育,同时也是给侵权人施加的责任承担的一种。第四关于赔礼道歉,实际上也是一种教育。在中国的执法中,赔礼道歉在生态保护中已经作为一种常见的补偿方式了,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在实践中加以使用,也应该是说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在诉讼费用方面,判决显然是做的有点过分。对于原告而言,表面上是赢了一千多元,实际上是赔了几千块钱,结果本来赢了官司,却不仅没拿到一千多元的生态利益费用,还要承担诉讼费。原告的计算依据法院可以不支持,但是诉讼费还判归原告方,这显然是对于公益诉讼的损害、对于制度的损害,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以上是我的看法,谢谢大家!整理/sakura审/泓嘉一编/sakura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chuanshanjiaf.com/csjxw/15035.html